在如今的求职市场,“空窗期”变成了敏感词,简历上的断档需要求职者想办法“粉饰”。“空窗”四年,她也编不出什么“自我提升”的借口。年龄和性别,让她对重返职场也不报太大希望:二十多岁时参加面试,HR问她有没有男朋友;现在她三十多岁,未婚未育,不需要再听HR的潜台词了。
近两年,社交平台出现“离职赛道”的话题:离开职场,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启人生。按照互联网思维,徐芳园本可为自己打造一份个人IP:靠着翻译副业轻松月入过万,一张书桌、一台电脑,比坐办公室打工好,再附上一条卖课链接。但性格不允许她这么做。
她将原书的一章节内容粘贴进文档,按段落,将中文写在英文上方,译完一段,校对修改,删去英文,接着重复操作译下一段,直到整个文档从全英文变成全中文,再打开新的文档,译新的章节。
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译者,徐芳园依旧没有形成“程式化”的工作方式。实际操作中,她努力逼自己,每天保持二三千余字的翻译量,几乎没有所谓的非工作日,连续工作两三个月,再出去玩几天。
公司换领导后,随之而来的是“拥抱变化”, 徐芳园的工作变成了机械式“内容搬运”和“洗稿”。领导要求员工加班,即使无班可加,她便留在工位上翻译,反正领导也看不出她在写什么。
初中时,徐芳园没有朋友,被同学孤立。她跑到图书馆,借了本厚厚的《尤利西斯》。1904年6月16日,它的作者、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与未来的妻子诺拉初次约会,漫步在都柏林的街头。120年后的6月16日,徐芳园在社交平台上宣传自己即将出版的第六本书——爱尔兰作家奥德丽·马吉的《他们涉海而来》。从年少爱上乔伊斯,到如今在自己译笔下看见爱尔兰,这是专属于她的奇遇。
用户对于某款APP的功能搞不清楚,她回复邮件进行解释;用户忘记了登入密码,她回复邮件帮忙重置;用户说有个亲戚去世了,需要接管亲戚账号,她回复邮件说需要上报处理;用户骂APP难用,问题怎么还没解决,她回复邮件说稍安勿躁,马上帮忙反馈,但她知道反馈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种不可控的工作内容让她感到崩溃,于是又起了离职的念头。经理找徐芳园谈话,问年近30的她,有什么职业规划?她想了想,之前的正职工作都在换来换去,只有翻译是有积累,且可控的。
这类资料查询的工作占据了徐芳园的主要精力,刚上手,一个晚上译不到1000字;到了周末,进度会快些,一个下午能翻译3000余字,算是破了自己的“历史记录”。周末上完法语课,她在图书馆或咖啡馆找个有插座的位置,敲击电脑键盘至天黑。
2013年,她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当老师、做外贸、进外企是当时的主流。那年初春,她考研失败,再冲进招聘市场时,已经没什么好的校招岗位。
在翻译《客居己乡》时,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损失七成的国土面积,让她觉得不可思议。花时间查资料,了解《特里亚农条约》和奥匈帝国与匈牙利的历史,才确认自己翻译无误。
通过社招,徐芳园进入北京一家由两个法国艺术家开的艺术教育培训机构当助理,那是她当时唯一能找到的位于大城市的工作。两个老板和一群老师之间,只有她一个非教学类的正式员工,行政、宣传等杂七杂八的工作均由她包办。刚入职,到手4000元的月薪,当年北京市的月平均工资是5793元。
到点下班,她不需要考虑工作上的任何事,剩余的16个小时都属于自己。关掉客服邮件,打开翻译文档,完成心态的切换,心甘情愿接受翻译的苦痛。
2019年初,她在一个翻译群看到招募《出埃及》译者的消息。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安德烈·艾席蒙,其另一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曾在2017年爆火。经过试译,徐芳园拿下了《出埃及》的翻译合同,24万字,千字100元。
赚钱少,也是摆在面前的现实。曾有人咨询徐芳园,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译者,她先劝退对方,千字80元,有经验的可能贵个20块,这是自由的代价。
2020年6月底,徐芳园第三次辞职,成为一名全职的自由译者。当年,上海月平均工资为10338元,这个数据和她再无关系。
“门柱圣卷下方是一块小小的金属匾额,刻着匈牙利在1914年的历史轮廓,在里面用纯黑色画着1920年的领土,仅剩原来百分之三十的大小,上面还写着标语“不,不,绝不!”——意为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这损失。”
人工智能的巨浪冲击着各行各业,翻译领域也不例外。为了赚点外快,徐芳园偶尔会接一些合同文书类等的商业翻译,机翻后再校对修改,基本一个下午就能交稿。对于文学作品,在她看来,AI翻译更像是对已有作品的搬运和拼贴,不知不觉地抄袭,不如自己翻译有意思。
2021年底,徐芳园一边翻译着《耶鲁需要女性》,一边准备托福和申请国外学校文书。最终,她没有收获那个能让自己重新置身校园的Offer。这个想法逐渐放弃,就像现在她也不再想着投递简历重回职场一样。
辞职后,生活圈也有所变化,用她的话说,是“从原本的郊区搬到更远的郊区”。她搬到了奉贤区,用2000块不到的价钱租了个大约30平方米的一室户,独居。
这份工作没有对接的“客户”,她的“社交圈”如愿缩小。工作日的白天,她在办公室写推文,下午6点下班,回到家开始翻译工作。
早在交译稿之前的2016年中旬,徐芳园就从教培机构离职了。那是微信公众号“风风火火”的时代,依托公众号起家的创业公司如雨后春笋,当年的微信公众号数量达到1777万。
安德烈·艾席蒙研究普鲁斯特,她找时间重读《追忆似水年华》,寻找两者相近之处;《出埃及》里有很多长句,她研究译者徐和瑾处理普鲁斯特的长句的技法,进而让自己沉浸在安德烈·艾席蒙营造的氛围中。
2020年初,徐芳园所在公司与外企的项目到期,公司把她调回办公室,负责管理技术类的客服团队,对客户反馈评分负责。若客户在评价时没有打满分,她需要分析原因,并培训团队的客服如何阻止“非满分”出现。
2016年,出版公司在为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的传记寻找译者,进度有点赶。“我之前看过契斯的书,还挺喜欢,就主动问编辑能不能交给我翻译。试译之后,他们让我接手了。”徐芳园记得,出版公司说,这本书难度比较大,稿费高点,千字85元。
在下一笔稿费到来之前,徐芳园会偶尔做点零工补充现金,虽然平时开销不大,现在也进入了消耗存款的阶段,这种“临时”能持续多久,她不知道。那些从事了一二十年的译者前辈,让徐芳园觉得翻译这件事可以持续做下去,至于更远的未来,不如走一步看一步。
小众,是她翻译作品的特点,在豆瓣读书的页面上,由她翻译的《客居己乡》只有363人标记读过,《抵抗的艺术》只有41人评分。
翻译一本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半年时间起步,不同于写作,需要译者紧随作者的意志,连续专注,就像长跑不能停,若稍微脱节几天,接下来的翻译过程只会越发想着放弃。
一本新书,从选题到摆上书架,大约需要18个月的时间,期间给到翻译的时间,从半年到9个月不等,有些出版公司的项目比较赶,20万字左右只留给译者4个月。
在上海,朋友介绍的工作,徐芳园也没抓住机会。第一个月,她先借宿朋友家,将手上的译稿赶完,之后在桂林公园附近找了间十几平的北卧,2100元的月租。
和文字打交道是徐芳园再次求职的首选。她曾为培训机构写公众号推文,凭着经验,很快找到一份新媒体编辑的工作,负责某个公众号的内容运营,税前8000元,当年北京的月平均工资是7706元。
摆脱上班的“痛苦”,也意味着要接受自由的“焦虑”,在她看来,所谓自由,不过是从一种束缚换到另一种束缚,“没书的时候焦虑要怎么接到下一本书,有书的时候焦虑翻译不完。”
事实上,让徐芳园困扰的翻译细节,读者未必在意。2021年8月,《出埃及》由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今,豆瓣上只有63人标记读过。同样由她翻译,《耶鲁需要女性》的读者稍微多一些,116人标记读过。
校译完成后,徐芳园主动问朋友有没有需要翻译的书稿。朋友发来《客居己乡》的英译版,她试译了一段,出版公司觉得挺合适,就把整本书的翻译工作交给她了,千字80元,译本出版后才付稿费。
一些译者同行日均五六千字,也有日译万字的业界传说,像正常上班一样的极度自律,她做不到。除了晚上专注的三四小时,剩余的时间都是她进入工作状态的准备期。
除了长句,她也会碰到一些不合常规的语句。《出埃及》里,有一个字典里不存在的词:blenkaw。联系上下文,是人物把blackout读错了。翻译思路就是先把blackout的意思翻译出来:“灯火管制”。再在“灯火管制”的基础上修改。思索片刻,她把blenkaw译为“登湖管子”,读音相似,但没有实际意义。
白天起床,她不用考虑上班迟到,没有家人在身边催促。吃早饭,学外语,看书,玩游戏,在沙发上无所事事地躺着,听窗外的鸟叫声,等阳光扫在身上。这些是她作为“社畜”时想要的奢侈和特权,也是她追求的“工作不饱和”的状态。
168体育全站2016年成为兼职译者,2020年成为全职自由译者,8年时间,徐芳园陆续翻译了10余本书,其中已出版5本,第6本即将问世。
欧洲的知识分子喜欢在写作中夹杂母语之外的外语,她正好学过德语、法语,遇到类似的语系词汇,也算是有个印象。实在翻译不出来的地方,在一些翻译群聊里咨询同行。
“会从事译者这份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小爱看书,或者说翻译文学。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但后来也没写出什么东西,既然学了英语,翻译文学作品至少和这个沾边。”徐芳园说。
徐芳园不爱社交,在教培机构需频繁和学生及家长打交道,小孩的吵闹也让她感到难受。没课的话,她不用一直待在办公室的电脑前;每年老板要回国度假,就顺道给她放一个月的假,工资照发。
她的周六,定6点半的闹钟喊自己起床,7点左右在江川路站坐上地铁,横跨整个上海市区的地下,在天潼路地铁站走上地面,赶在9点前抵达上海的法盟,学习5小时的法语。下午3点,再从地铁站走入地下返程,回到住处基本上是5点,身心疲惫,晚上给作为译者的自己放个假,周日再翻译一整天。
翻译是徐芳园的擅长。对她来说,出门上班是逼自己跳出舒适区的方式,她试过很多次,最后发现,还是更喜欢待在家里,多认识些编辑,多译几本书。
收入是绕不开的现实。文学翻译从来都不是一份可以养活译者的工作,部分译者用一份赚钱的工作来供养这份“爱好”,上了年纪,精力跑不过热情,就 “退圈”了。
小时候,徐芳园很向往卡夫卡的理想生活:住阴暗、潮湿的地窖尽头,不用出去,每天有人把饭送到门口,因此也不用跟任何人说话。现在想想也算是实现了,虽然她不住在地窖尽头,但确实可以一整天不用出门、不用跟人说话。
直到2017年10月,她找到第三份正式工作,为一家世界500强外企做外包英语客服,即回复英文邮件。这份工作不要求坐班,每天上线工作8小时,完成自己的“覆盖率”即可。月薪和上份工资持平,依旧是8000元,当年上海的月平均工资是7132元。
徐芳园很少出门。翻译需要全神贯注,等窗外的天空完全暗下来,她才坐上面墙的书桌,打开电脑,戴上降噪耳机,听着白噪音,手机屏幕朝下。
主动选择背后也有焦虑。在她看来,所谓自由,不过是从一种束缚换到另一种束缚,“没书的时候焦虑要怎么接到下一本书,有书的时候焦虑翻译不完。”
图书编辑为一本书寻找合适的译者,除了要考察译者的翻译水平,还需确认译者有没有足够的耐心能坚持。合作过的靠谱译者是编辑首选,没合作过的,最好有同行编辑的“担保”引荐。绝大部分译者,即使译作等身,想要获得更多机会,就得想办法被更多的编辑看到,然后等待被选择。
进入一个行业,干到退休,是一种理想状态。一个人脱离职场,在坐进下一间办公室之前,这个人就处于一种“临时”的状态。签下一本书的翻译合同,徐芳园便会为这本书规划接下来的生活,将自己的“临时”状态顺延。
文学翻译如何养活自己?徐芳园算过一笔账,按照每千字80-100元的稿费标准,要保持和上班持平的收入,每天需要翻译4000字,每月工作20天,现实中她很难做到。
为不让自己闲着,徐芳园决定找个兼职。网上有招募图书译者,她试着海投。正巧,朋友所在的图书出版公司招兼职编辑,简历通过了,但出版公司没有书稿给她编辑,只有本需要再版的译稿,因为两个译者的风格不统一,找她做校译。
大桥东侧是西渡小公园。午饭结束,年长者陆续至此,绕树而坐,唱歌、下棋或者单纯地发呆至太阳落山。步行15分钟即西渡渡口,轮渡往返于闵行、奉贤之间。
对一个比较宅的人来说,住的地方大一些,比住得离市区近一些更重要。毕竟在桂林公园对面住了近一年,徐芳园没走进去过一次。2018年,她搬去了老闵行,和陌生人合租。从上海的中环内来到郊区,更大的房间,更便宜的租金,一个月1600元。
翻译的书陆续出版,和更多的出版公司建立联系。之前合作过的编辑会继续给她推书,也有陌生的编辑在豆瓣上私信她询问合作意向。有时候,项目没确定,编辑就找她,说书的版权签约还在走流程,能不能预定她的时间。若一个项目周期很长,她可以同时接下两本书的翻译工作,虽然以她的习惯,仍是译完一本再译下一本,但只要制定好工作计划,时间调配得当,她现在有得选。


 换一换
换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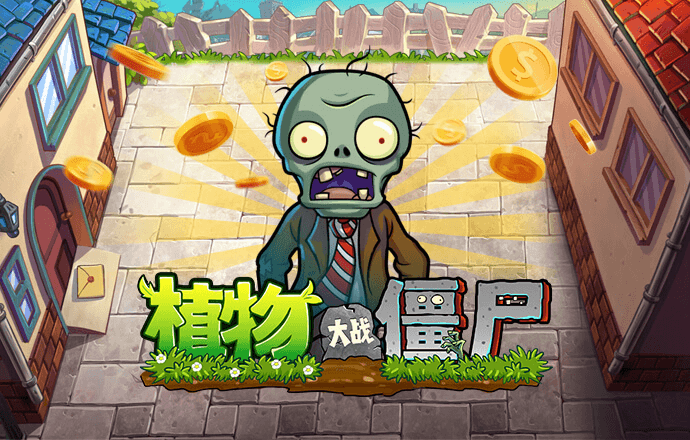












 168体育全站 v1.1.6官方正式版
168体育全站 v1.1.6官方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