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高校被退档的专业均标注着(不招色盲、色弱考生),所以想要报考上述高校的考生,要根据自己身体情况谨慎填报。
此外,公费专科医学生、高职院校专项计划、“3+2对口贯通分段培养”高职阶段招生均包含在96个志愿之内,符合条件的考生可在常规批第2次志愿填报时填报。
宝博游戏大厅7月22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2024年普通类常规批(本科)第2次志愿院校专业计划。海报新闻梳理发现,山东普通类常规批(本科)第1次志愿投档后,还剩余超过7000个本科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实行新高考以来,山东剩余本科计划最多的一年。对此,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与山东今年首次实行物理化学捆绑填报志愿有关。
在7月22日举行的山东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放日现场,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副院长赵丽也强调说,普通类常规批第1次志愿填报未完成的计划,主要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她还进一步解释说,近年来,国家对理工农医类人才需求大量增加,各高校也积极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持续增加理工农医类专业招生计划,并根据培养高质量理工农医类人才的需要,对相关专业提出了物理和化学等选考科目要求。
而考生要注意的是,这些新增招生计划高校中有多所高校都对高考分数进行了限制。像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新增的3个招生计划中,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要求文化课成绩不低于562分,工程力学专业要求文化课成绩不低于559分、工商管理专业文化课成绩不低于563分。
同时,在普通类常规批(本科)第2次志愿院校专业计划中,河北师范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天津城建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湖北经济学院、郑州西亚斯学院、广西外国语学院、武汉城市学院、三亚学院等9所高校还新增了30个招生计划。其中,湖北经济学院新增12个招生计划,为新增招生计划数最多的高校。
2024年普通类常规批(本科)第2次志愿院校专业计划显示,130余所高校还剩余超过7000个本科计划。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些剩余本科招生计划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第一类是第1次志愿未投满计划,第二类是因退档而空出的招生计划,第三类是院校新增招生计划。
赵丽表示,按照工作安排,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普通类特殊类型批和常规批第1次志愿录检,艺术类、春季高考第2次志愿录检。分别于7月22日下午4点、7月23日上午11点后公布录取结果。接下来,山东还将依次进行普通类及体育类常规批、艺术类、春季高考的相关批次志愿填报录取工作。
特别要关注的是,这些新增招生计划中,除天津城建大学的交通工程专业、湖北经济学院的金融工程专业、武汉城市学院的工程造价专业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三亚学院的金融科技专业外,剩余专业并未对选考科目进行限制。
海报新闻记者了解到,按照山东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安排,普通类常规批第2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4日—26日(每天9:00—18:00)。需要注意的是,此前划定的山东省夏季高考一段线不是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而是分段填报志愿的资格线。赵丽说,在普通类常规批第2次志愿填报时,达到普通类二段线(150分及以上)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同时填报本科缺额计划和专科志愿计划。
不过,与新增招生计划相比,第1次志愿未投满计划对未选考物理和化学的考生就不太“友好”了。海报新闻记者注意到,除去退档和新增招生计划,剩余招生计划几乎都只限选考物理和化学的考生才能报考。
在7月22日举行的山东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开放日现场,赵丽说,截至目前,山东已顺利完成提前批以及艺术类本科批、体育类常规批、春季高考本科批第1次志愿录取工作,共录取考生76845人。其中,提前批13425人,艺术类本科批36381人,体育类常规批5421人,春季高考本科批21618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剩余招生计划均为选考“物理+化学”。对于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新高考模式下,选择文科类考试科目的人变多了,但高校各专业招生计划较之前并未做出明显调整。今年,山东又实行“物理+化学”捆绑,这也导致仅选择物理或者化学的考生涌向文理兼招专业,对传统文科考生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因退档而空出的招生计划中不乏入选“双一流”计划高校,分别是:东北农业大学被退档1人,广西大学被退档1人,海南大学被退档1人。此外,因退档而空出招生计划的高校中也不乏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北部湾大学等区域重点高校。
2023年普通类常规批第1次志愿计划完成率高达99.99%,仅有9所高校剩余13个招生计划。不过,今年山东普通类常规批(本科)第1次志愿投档后,还剩余超过7000个本科计划。海报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剩余这些招生计划中,有12所高校剩余招生计划数超过100个,分别是:潍坊理工学院剩余303个招生计划,齐鲁理工学院剩余572个招生计划,青岛工学院剩余427个招生计划,山东华宇工学院936个招生计划,青岛城市学院485个招生计划,烟台理工学院682个招生计划,山东协和学院473个招生计划,青岛黄海学院431个招生计划,青岛恒星科技学院310个招生计划,山东英才学院282个招生计划,潍坊科技学院163个招生计划,青岛滨海学院694个招生计划。


 换一换
换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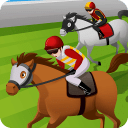





 宝博游戏大厅 v3.3.7官方正式版
宝博游戏大厅 v3.3.7官方正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