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深刻的是,高中同学吴绍基向其介绍并讨论刊登在《青年知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章从当前民族危亡、人民苦难深重的大环境说起,强调青年对理想和前途的追求,只有在投入人民大众挽救危亡、挣脱苦难、争取独立和生存的斗争中才能实现,青年应当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如果脱离了民族和大众的利益而只求个人的出人头地,不但难以实现,弄不好还会做出与本来的善良愿望相违背的事来。
老钱坚持定期参加党组织生活,再忙每月总是按时缴纳党费。“有时工作实在走不开,就把钱交给我,嘱咐我去党委交党费。”纪德来曾在《给钱李仁社长当司机兼秘书》一文中写道:钱社长平时言语不多,见到熟人点点头,似乎与人保持距离;实际上内心温暖,对下属有很深的保护意识,遇事挺身而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1939年12月,钱李仁在吴绍基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他说,自己从原来只是关心时局、讨论时局的“学习者”向着把自己“摆进去”,做一个愿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事业付出努力甚至牺牲的 “工作者”跨出了第一步。
文章把这两种选择进行了通俗对比,并用许多生动实例来说明。钱李仁觉得,这与自己在不久前经历的“逃难”中所见所闻所感很对得上号,同时又扩大了其思想境界,把对时局的关心同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思考紧密联系了起来,“这可以说是我在走向革命的道路上第一次思想上的飞跃”。
纪德来回忆,在首次全社职工大会的履新讲话上,老钱坦言,“除了一位司机,我一个人也不带进报社!”并鼓励大家继续解放思想,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还承诺将秉公办事,一碗水端平,不会任人唯亲。
1988年,《人民日报》经济部记者蒋亚平采写的调查报道见报——《“丰收”的折扣》,批评某地郊县在推行规模经营旗号下,动摇包产到户政策,虚报粮食产量。同时,为了搞规模经营,还撕毁了与农户签订的果树承包合同……报道刊发后,当地县长打来电话,威胁说会有农民进城到报社门口抗议。
“父亲一辈子严谨,最佩服老人家的自律,已经到了让年轻人看来简直疯狂的地步。”老钱儿子钱亚飞说,之前,每天上午9点、下午3点,他一定要出家门散步。假如我们手头还有点事,跟他说过5分钟咱们再出去,他就会像小孩一样,差不多每分钟都会走过来,在你面前晃一晃,催促出门。出去散步一共30分钟,从出门就开始唱歌,第一首一定是“长亭外古道边”,最后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一定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而且最后的一个字“杀!”一定是“杀”到家门口。
1964年,历时25年的青年工作战线“毕业”,钱李仁先后被调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友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联部等机构工作,直到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社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大打内战,反对国民党的卖国、独裁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失学、失业与饥饿,展开了前赴后继的斗争。上海学生多次冲破阻挠、镇压,上街示威游行或举行罢课。
在回忆录中,钱李仁说:“1935年12月,我作为初中一年级学生,参加了本校高年级同学所组织的响应平、津学生一二·九运动的部分集会,这是我步入当年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开始。”
“老钱,您今年多少岁呀?”百岁生日前夕,记者前往医院探望这位世纪老人,他笑言自己已经“156岁了”。尽管言语含糊,听力下降,但他依然可以复述出来访者的名字,眼神也格外清澈透亮,可以顺畅读出《人民日报》刊载的新闻标题:“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
当时,钱李仁的一位表哥在南京上初中,订了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每逢寒暑假回镇江时就会极力向他推荐,“我很快为它许多独到的报道和立论所吸引,成为其长期订户,韬奋先生真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钱李仁坦言,自己刚读高一时,并没人来领导鼓动,“但是我自己发自内心地,已经充满了抗日的想法”。
在一封亲笔信中,钱李仁如此透露心声:“从年轻时就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投身于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投身党的青年及外事工作;在经受了‘文革’的动荡与冲击后,受党和国家委派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一次投身外事工作。1982年调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1985年年届61岁时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我将所经历的丰富多彩的人生的一些点滴和感悟及历险记录了下来,希望与同事们、朋友们分享。”
“自己上了一堂群众工作的基础课,学到了一点儿做好任何工作都需要的基本功。”钱李仁说,在此过程中,吴绍基逐步启发其思考入党问题,随后在望志路(今兴业路)吴家阁楼,举行了入党宣誓。此后,他积极投身地下革命,发展新党员。1942年,上海中学党员达50人,钱李仁组织领导多起学生运动,成为斗争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直至迎来解放。
未满13岁的少年,在兵荒马乱的火车站坐到天亮,第二天中午才回到出生地嘉兴王店镇。这是钱李仁记忆里的第一次逃难,“就这样停停走走,到苏州车站时天已全黑。列车刚停靠,以苏州为目的地的旅客还在陆续下车,车站上空就响起凄厉的空袭警报声:上海已经开战。”
很长一段时间,钱李仁希望别人称呼他“老钱”,曾有人亲见他当面直言:“不要叫我钱老,叫老钱!这是第三次纠正你了,达成协议。”问他为什么?自在些。
十年前,九十高龄的老钱在电脑前,一字一句地敲出了自己的回忆录《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这本书记录了他从幼年时代起学习、成长,参加革命队伍,直到1985年岁末到《人民日报》任职所走过的人生道路。
这一不计个人得失的坦荡,令人感佩至今。“老钱从报社退下30多年了,人们还记着他,能赢得这种待遇的,极少极少。”吴长生说。
1937年8月13日,钱李仁一家五口,从镇江坐火车逃往嘉兴。这一天,日本侵华战争在上海的战事正式爆发。当时,北平已沦陷,日军南北全面侵华的态势已经摆开。镇江作为当时江苏省的省会,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何早日离开,成为摆在钱父眼前的难题。
1947年11月起,钱李仁到“上海学联”任党组书记,并于1948年7月任学生运动学委委员。“我现在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当年在上海这段岁月。我们虽然没有扛起枪杆,不是直接打仗,但就像毛主席曾经评价的,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钱李仁说。
报道刊发后,有关方面坚持认为报道失实,给当地农村发展带来困难,要求刊登更正报道。面对重压,老钱则提出:本报的报道基本事实准确,应该严格执行中央政策,维护合同的严肃性,保持家庭联产承包制稳定,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切实纠正不当做法。
1985年12月的一天,一位头发花白、挺着笔直腰板的长者端着饭盒在《人民日报》大食堂排队打饭。就在几天前,年逾花甲的钱李仁带着中联部机要通讯班班长纪德来前往报社履新。
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事多繁忙、责任重大,但老钱并没有什么“特权”,照样得去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到中央开会,回到报社食堂,饭菜已经凉了,他就在简陋的社长办公室里吃上几口充饥”。纪德来回忆,为节省时间,特别是在吃饭和理发时,他经常帮着老社长排队,快轮到时,再喊他过来,对于部下的谦让,他并不肯接受。“我给钱社长开车每天早出晚归,有时一连几天我的小孩都看不到我,钱社长的辛苦更可想而知。”
解放前夕,钱李仁接通知分配到上海市青年委员会系统工作,“这样,从1939年12月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学协’算起,在党领导下近九年半的地下工作画上了句号”。
曾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仁臣回忆,老社长刚上任就希望大家叫他“老钱”,他的办公室,编委会成员可以进,部主任可以进,编辑记者可以进,印厂工人也可以进,只要你感到有充足的理由。“这些看似小事,却深得人心,因为大家感到被信任、被尊重,来了一位有水平又平易近人的领导。”李仁臣说。
对国事关心度的“发育”远远超过年龄增长速度,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这个最大的反面教员催发出来的那一代青少年政治上的“早熟”。当然,小小年纪要早熟懂事,光有反面教员是不够的。
allbet手机版仁者已期颐。8月20日,是人民日报社老社长钱李仁百岁上寿的日子。因年事已高,这位世纪老人住进了北京医院,谨遵医嘱,静心休养。
老钱还做过中联部部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过首任大使衔中国代表,是一位有国际视野的领导干部,纵使历经兵荒马乱的年代,仍然秉持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
退休之后,老钱的生活回归平静,但仍存少年心境。十年前,他在电脑前一字一句地敲出了一本回忆录《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这本书记录了他从幼年时代起学习、成长,参加革命队伍,直至前往《人民日报》任职所走过的人生道路。
如此熙熙攘攘一个多月,日军于当年11月5日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继而迅速占领上海,分头向南京和杭州推进,王店、镇江均已危在旦夕。此时,钱家决定二次逃难,北上高邮。但紧接着是镇江沦陷、南京沦陷、扬州沦陷,日军直逼高邮。钱父最终决定投向上海一位表亲所在的公共租界。
“从高邮,走水路,乘船经兴化到泰州,再从泰州走陆路,经过黄桥到长江边的新港,搭乘去上海的轮船。”关于这一段行程,14岁的钱李仁曾在《文汇报》发表署名为“仁”的文章,表达对于侵略行为的“无限的痛惜,愤慨”,该文结尾写道:“轮船顺利地到了上海,战争的遗迹——断垣残壁仍旧留存着。浦江中一只只的船上,都像贴上一张张膏药一样。踏上了‘孤岛’,又看见行人如蚁、车水马龙的升平景象了。”
1940年,钱李仁正式入党。解放前,他是上海地下党学联党组书记。1949年后,他在团中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中联部长期从事外事工作;1985年12月,老钱出任人民日报社长,自称“六十学吹鼓”。1996年,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
有一次,钱李仁进报社编辑部大楼,被驻社武警门卫阻拦,要检查证件。他正在掏证件时,报社保卫处同志赶过来,批评武警无礼。老钱却拦住说:“不该批评,应该表扬,这是对报社安全认真负责。”
“我们总讲政治家办报,什么样子?老钱让我见识了。”吴长生深有感触地说:老钱虽不是传统的报人,但却是个高水平的报社掌舵人,“立场坚定,独立思考,坚持原则,勇于担当”。
解放后,钱李仁先后在“中共上海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任职,随后和夫人一起前往北京,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直至外派至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担任书记。
加入学协后所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反汪斗争”。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天,上中学生举行反汪大会,“基本做到全校发动”,震动沪上各界。随后,全市百余所大中学校发表声明:绝不承认汪伪政权。此后,一家权威媒体刊发报道:《上海学协,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旗帜》。
“镇江是我至今魂牵梦萦、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1937年秋,钱李仁进入镇江师范学校初中课堂。彼时,学校的老师、同学,从课内到课外,都在关注、议论乃至辩论着抗战的形势和前途。
上任伊始,钱李仁用了很大精力与报社干部职工进行交流,倾听意见。到任最初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里,他的笔记本上列有与之分别谈话的43位同志的名单,其中大部分人各谈一次,有些人谈话两次,个别的有三次,还走访了编辑部的一些部门以及工厂、食堂、幼儿园。
他说,这一段逃难生活可以说是在社会这个大学里上了两堂课。一堂是从国难家仇、自身的颠沛流离和目睹最底层大众的苦难中深刻感受到民族独立和社会公平之重要;一堂课是从所接触到的革命的、进步的师友和书刊中逐步开始思考改变现状的前景和道路。“这为我下一步的继续前进打下了重要基础。”在此之后,钱李仁开始了长达15年的上海岁月。
可想而知,当时的舆论监督难度之大。在办报理念上,钱李仁曾如此阐述: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来做有说服力的,有生动内容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正面宣传。批评性的要不要?还是要。但是目的不是给人以一团漆黑的感觉,不是使人丧失信心,要使人看到我们有力量克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下笔是一字千钧,不是闹着玩的,不是灵机一动”。
因关系重大,老钱叫来了时任经济部农村组负责人吴长生,详询报道依据。吴长生送上记者的采访笔记等一大摞资料,老钱为此窝在办公室整整看了一天。1989年1月2日上班后,他对吴长生说:“如果打官司,我钱李仁上法庭。”
“在镇江登车也还不知道上海已经打起来。只是一路上我们所乘的客运列车常常在小站停靠,让满载着士兵和军器的列车超过我们向上海方向飞驰而去。”钱李仁回忆说,看到全副武装的中国兵开赴前方,既振奋又预感要出事,这种感觉至今犹在。
不久后,因日军攻占上海计划受阻,镇江方面也从战事初起时的慌乱中镇定下来,学校宣布九月正常开学。后来,钱家又乘火车循来时原路回到镇江。


 换一换
换一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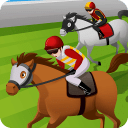














 allbet手机版 v5.1.5官方正式版
allbet手机版 v5.1.5官方正式版